欢迎您访问米乐M6(MiLe)亚洲官方网站轴承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 HASHKFK


 新闻资讯
新闻资讯 米乐M6娱乐
米乐M6娱乐米乐M6(MiLe)亚洲官方网站- 赔率最高在线投注平台(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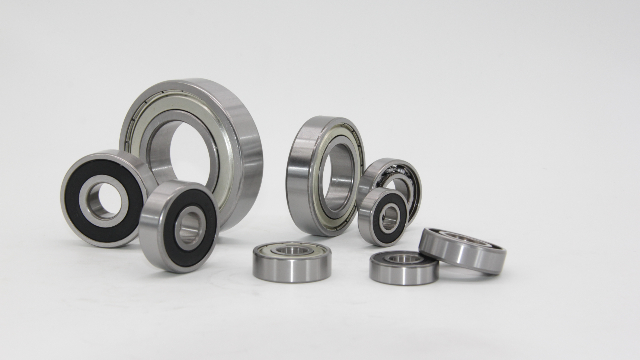
只有对等关系的义务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如果不是对等关系的义务,就不能适用先履行抗辩权。《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题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还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民法典》这些规定中都提及了“主要义务”“主要债务”的概念,所谓主要义务米乐M6(MiLe)亚洲官方网站- 赔率最高在线投注平台,一教是指根据合同性质面决定的直接影响合同的成立及当事人订约目的的义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主要义务是一方交付标的物,另方支付价款。合同中主要义务的特点在于,主要义务与合同的成或当事人的缔约目的紧密相连,对主要义务的不履行将会导致债权人订立合同目的的无法实现,债务人的违约行为会构成根本违约,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在双务合同中如果一方不履行其依据合同所负有的主要义务,另一方有权行使抗辩权。《民法典》第七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由此可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主要义务就是一方完成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另一方依约支付工程款项。而开具发票的义务显然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主要义务,一方当事人违反该义务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仅仅因为未及时出具相应发票而主张解除合同,也不能仅因此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委托人(建设单位)或者使用人没有作为发包方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如果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委托人(建设单位)或者使用人直接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设计变更施工方案或者增减工程量并直接对承包人进行指示、参与施工现场管理等情形,足以认定委托人(建设单位)或者使用人已经加入建设工程合同的履行中,承包人起诉要求委托人(建设单位)或者使用人与代建方共同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代建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承包人订立的施工合同,承包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代建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建关系的,根据《民法典》第925条的规定,该施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承包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代建人和承包人的除外。根据委托代建合同约定,代建人享有对委托人(建设单位)或者使用人代建费用债权,承包人如果认为代建人怠于行使该债权影响其到期工程价款债权,依照《民法典》第535条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在查明相关案件事实后作出相应的裁判。
关于案涉工程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郭福发虽在《施工班组/分包单位工程结算单》上确认:“承诺待业主方支付至工程款的总额95%时,甲方给予结清款项”。但是,本案中,业主方是否向协胜公司支付至工程款的总额95%,与郭福发、林安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林安公司亦未抗辩称协胜公司未依约向其支付工程款。林安公司与郭福发签订的案涉《工程劳务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法律规定,除争议解决条款外,其他条款也应无效。而付款条件不属于争议解决条款的范畴,故林安公司与郭福发关于付款条件的约定,亦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因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现郭福发要求林安公司偿付尚欠的工程款343023.36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2020年9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当事人往往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工程款付款条件,但在诉讼中,关于付款条件的合同条款是否有效经常存在争议。此种情形下,首先,应当审查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如果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而被认定无效,除争议解决条款外,其他合同条款也应无效。其次,从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虽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已完工并经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承包方有权依照该规定要求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计算标准赔偿损失。发包方通常也会以上述规定为据,抗辩付款条件也应参照合同约定。我们认为,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上是针对合同无效后进行折价补偿的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参照合同约定”是确定折价标准的一种方式而已,不等同于“按照合同约定”,不是按有效合同处理。应对“参照合同约定”作严格的限制解释处理,即仅限于合同中对工程价款计算标准的约定,而付款条件、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以及工程款减扣等,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的参照范围。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承包方的交付竣工资料义务与发包方的工程价款支付义务不具有对等关系。发包方仅以承包方未交付竣工资料为由抗辩阻却承包方支付工程价款请求权,不能成立。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方未及时交付竣工资料,发包方有权拒绝支付工程价款。该约定视为当事人一致同意将交付竣工资料作为与支付工程价款同等的义务,未交付竣工资料构成拒付工程价款的抗辩事由。但仅是约定承包方逾期未交付竣工资料应支付违约金并在未付工程价款中扣减,并没有明确约定交付竣工资料作为支付工程付款的条件,应当认为双方未就交付竣工资料与支付工程价款系同等义务达成一致意见,发包方以承包方未交付竣工资料为由抗辩支付工程价款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审判实务中,发包方经常以承包方未履行交付竣工资料等协作义务为由,作为拒付工程价款的抗辩,但由于两种义务性质不同,发包方的抗辩一般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法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当事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在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新的安排。竣工资料涉及合同项下已完工程的产权办理,关系发包方资产盘活和融资。因此,当事人明确约定:承包方未及时交付竣工资料,发包方有权拒绝支付工程价款。在此情况下,未交付竣工资料构成拒付工程价款的抗辩事由。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8月28日签订案涉《协议书》,设定恒大公司未依约交付竣工资料的违约责任,但并未明确约定交付竣工资料作为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条件,故兴龙公司以恒大公司未交付竣工资料为由,主张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
首先,关于本案涉及到的合同相对性问题。所谓合同相对性,即合同效力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只对特定主体发生约束力,即其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合同外的第三人既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义务;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基于合同相互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合同当事人不能依据合同对合同关系外第三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也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具体到本案中,丁公司与丙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与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甲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之间均不存在合同关系,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只能向合同相对人丙公司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而不能向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主张工程款。
其次,关于丁公司主张的连带责任问题。丁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其合同相对人之外的甲公司、乙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主张权利,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从该两款规定可以看出,实际施工人提起诉讼主张工程款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以突破合同相对性为特别规定。该特别规定意在保护农民工等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施工资质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者结构施工的劳务分包企业等。本案中,丁公司作为具有涉案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经与丙公司签订涉案弱电工程施工合同,负责涉案保障楼、科研楼、检测中心、办公楼综合布线系统、监控系统、一卡通系统,保障楼有线电视系统和门铃系统的辅材采购、施工、安装、调试,所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作业而非普通劳务作业,且被拖欠的系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故其要求乙公司及其青岛分公司、甲公司和青岛某研究院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海天公司向盛泰公司发出的《联系函》,案涉项目工程款必须汇入海天公司云南分公司指定基本账户,汇入其他账户海天公司不予认可。盛泰公司收到《联系函》后应对该函件内容明知。在该种情况下,盛泰公司仍然将上述款项2313万元支付给吴XX,不能当然认定该2313万元系支付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如盛泰公司仍主张该款项为支付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其应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系用于案涉工程施工。在合议庭当庭就此向盛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释明了其举证证明责任后,盛泰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支付凭证或者款项用于案涉工程的证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盛泰公司并未完成该2313万元系其支付案涉工程工程款的举证证明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该2313万元不能被认定为盛泰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益华公司和中建七局一公司之间的案涉施工合同已在全部工程竣工交付前解除,但双方在2015年4月23日已通过会议协商的方式决定于2015年4月24日至4月28日由双方核对工程量及款项支付、应付未付款项的支付方案、结算和收尾工程施工及竣工验收工作等事宜,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应视为双方此时达成了结算的合意,原审据此认定双方核算的最后一日即2015年4月28日为案涉工程应付款之日,亦无不当。益华公司与中建七局一公司约定工程款以进度款方式支付的前提是案涉施工合同能够完全履行完毕。但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表明案涉施工合同已无继续履行之可能,双方已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在此基础上,益华公司应承担已完工工程款的足额给付义务,原审认定益华公司应全额支付已完工工程款正确。本院对益华公司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盛泰公司明确收到海天公司通知的情况下,盛泰公司仍将案涉2313万元款项支付给案外人吴某某,而与《联系函》通知之履行方式不一致,除非盛泰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实际用于案涉工程施工或者该给付行为被海天公司所追认,否则不应认定为用于支付案涉工程款。对此,盛泰公司提出2014年3月15日,海天公司就资金成本折算事宜向盛泰公司发出《联系函》,声明“春节前甲方(盛泰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6300万元整,尚有余款4500万元整未予支付”。盛泰公司提出该6300万元包含了2013年12月6日后盛泰公司直接向吴某某支付的550万元及盛泰公司代偿的巴某某对吴某某的工程借款500万元。因此,通过海天公司在3月15日《联系函》中将该两笔款项计入海天公司已收工程款的行为,可以推断海天公司已经实际认可了吴某某代海天公司收取工程款的权限,基于对吴某某的这种合理信赖,盛泰公司后续向吴某某支付的1263万元款项亦应当计入工程付款。本院认为,首先,3月15日《联系函》并未提及前述550万元、500万元两笔款项,仅从3月15日《联系函》内容本身来看,无法得出前述550万元、500万元两笔款项包含在已付工程款总额6300万元之内的结论。其次,盛泰公司提交的“附表四、自开工后至2014年1月31日(春节)前盛泰向海天支付工程款”明细汇总后数额虽与6300万元对应,但该明细表系盛泰公司单方面制作形成,是否真实、全面反映海天公司与盛泰公司在2014年1月31日前的工程款支付情况无法确认。第三,3月15日《联系函》并非是工程款结算函,并不具有结算功能,亦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工程款支付情况的依据。因此,盛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前述550万元、500万元两笔款项已经为海天公司所认可,亦无法证明海天公司对吴某某的收款行为予以追认。此外,盛泰公司提交了2014年5月30日吴某某的银行交易记录,交易记录显示吴某某在收到盛泰公司项目负责人朱黎光向其转入的250万元款项后,立即将该笔款项全数转入海天公司账户,用以证明吴某某系代海天公司收取款项。然而,银行流水仅能证明特定时间节点的资金流向,并不能证明资金之用途以及背后的基础法律关系。因此,仅凭银行转账流水单并不能证明系吴某某代表海天公司收取款项,亦不能证明该250万元系用于案涉建设工程。因此,盛泰公司再审申请所提交之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至于盛泰公司与吴某某经济往来应依法另寻途径解决。
弥河林场主张刘洋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并提交了刘洋与伟达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等证据材料,该材料系合同复印件,落款签订日期为2010年9月25日,早于涉案工程邀请招标以及伟达公司中标时间,弥河林场对此未作出合理说明,且伟达公司亦不认可刘洋为其合同相对方,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总体而言,弥河林场已付8千余万款项中,除100万元工程款为弥河林场支付给伟达公司以外,其余大部分工程款为案外人刘洋等人持加盖伟达公司字样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至弥河林场处领取,伟达公司对此亦予以追认,故弥河林场尚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刘洋与伟达公司存在直接的实际施工关系。弥河林场应将欠付工程款依约支付给合同相对方伟达公司或受到伟达公司委托的人,在未经伟达公司确认的情况下,弥河林场认可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的1052万元,不能作为弥河林场已支付的案涉应付款项。对于该扣划的1052万元工程款,弥河林场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是否达成了以物抵债协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本工程竣工后,结算审核完成后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蒙奇公司不能按时按量的支付和兴公司工程款时,蒙奇公司可以将已竣工的可以投入使用的成品(如商场以及产权式酒店)等,按欠付的和兴公司工程款等价转交于和兴公司名下,转交价格按当地市场行情下浮15%。”如果双方达成以商品房抵偿工程欠款的协议,必须具备清楚明确的债权的数额、用以抵债的房屋的位置、面积及价格。但当事人在签订上述补充协议时,案涉工程刚开始施工,双方尚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房屋亦未建成,以物抵债协议应当具备的基本内容均未确定。且从双方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可见,在蒙奇房产公司给付的工程款中,存在以建成后的商品房抵偿的情况,双方另行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在该合同中对房屋的位置、面积及价格做出清楚明确的约定,从而确定抵偿的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因此,案涉《补充协议》不具备以物抵债协议的基本内容,不能认为双方就案涉工程欠款达成了以商品房抵偿的合意。
合同具有相对性,无论是否存在承包人以外的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交付工程的义务人为承包人,相应地,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亦是发包人的合同义务。当然,在存在实际施工人的情形下,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建筑工人的权益,相关的司法解释突破合同相对性,赋予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的权利,但发包人仅在欠付承包人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付款责任。其引申含义为,若发包人已经向承包人支付完毕全部工程款,则无需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亦即,在存在承包人以外的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否定承包人依据合同约定向发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的权利。因此,本案中,即使存在实际施工人,三建公司仍有权依据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请求支付工程款。二审判决认定三建公司系请求支付工程款的适格主体正确。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体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建设工程标的额巨大,不同计价方式对当事人利益有较大影响。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当事人对工程价款的结算,可能采用固定价格、可调价格,或是成本加酬金等几种方式。法律不限制当事人自由约定工程计价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因工程款计价方式产生纠纷的时候,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按照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确定工程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即便合同解除,双方约定的工程款的结算方式属于合同中的结算条款,仍然有效,应当得到执行。事实上,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即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也可以参照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计算方式确定工程款,这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价款纠纷中对当事人约定计价方式予以充分尊重的的体现。本案体现,当事人约定的工程款计价方式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当事人应当对此高度注意。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三建公司上诉提出,三建公司从未委托余卫德向凯创公司借款或者领取工程款,合同约定了工程款专户,专款专用,余卫德收取的15,000,000元与三建公司无关。经查,余卫德向凯创公司收取了15,000,000元,出具了7张借条、1张收条,其上均加盖有三建公司项目部印章。收条载明:“今收到凯创公司陈杨新界项目工程款5,000,000元整,此款汇入余卫德建行卡6217×××”。凯创公司在借条、收条后均附《月度工程款支付分配核定表》,并备注:“根据余总(余卫德)要求和建议本次付款可否直接支付其个人,以减少三建公司扣除管理费和其他费用,以便能全额付给工人,杜绝工人滋事。”余卫德2018年8月28日、9月27日在接受西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六大队询问时,陈述三建公司知悉该15,000,000元,并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给供货商付款及支付项目管理人员工资。本院认为,双方合同虽约定了专户,但前述事实表明余卫德领取的15,000,000元已实际用于案涉工程,一审判决将该笔款项计入凯创公司已付工程款,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第三人代为履行中,其并非合同当事人,合同亦无权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其是否履行债务纯属自由。而本案中,建设单位作出了承诺,加盖了印章,成为了合同当事人。因此,认定第三人代为履行不妥当。同时,也不宜认定为债务加入或者提供保证,因为无论是担保还是债务加入,均有用自身的责任财产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而从这承诺背景来看,建设单位显然没有这个意思表示,其本意是用欠施工单位的工程款代偿供应商的货款。关于好意施惠的观点,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相悖。假若认定建设单位作出了承诺却不受任何约束,显然违背了正常人的通常观念,违背诚信原则,也将使得承诺成为“一纸空文”。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何认定的问题。昌泰源公司上诉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承包人对建设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是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且经承包人催告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工程款发包人仍逾期不支付。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那么有关支付工程款的约定自始无效,上述两个前提条件也就不能满足,且法律和司法解释从未规定承包人对根据无效合同原则应取得折价补偿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此甘肃一建不应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规定的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一项法定权利,目的是保障承包人能够优先获得工程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并非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条件。